從漢代鎏金銅馬品味馬文化
從堂吉訶德騎的那匹羸弱老馬到唐僧取經路上的好腳力白龍馬、巨人卡岡都亞的大牝馬,再到南美解放者西蒙·玻利瓦爾雕塑中那前蹄凌空的戰馬……可以說,馬文化是世界文化里密不可分的一部分。從戰場到農田,從宮廷到賽場,與人最密切、最親近、最能溝通交流的動物就是馬。讓我們隨著長安塔上展出的國寶文物——漢代鎏金銅馬,去感受源遠流長的馬文化。

鎏金銅馬藝術價值極高,其通體鎏金、表面光潔,馬尾及生殖器另鑄鉚接或焊接,馬尾根高聳成弧形下垂。該銅雕馬身中空,高過半米、重約50斤,作直立狀,昂首翹尾。從其緊縮的腹部、結實的肢體來判斷,應是乘用馬。該鎏金銅馬出土于茂陵附近,與漢武帝之姊陽信公主與丈夫衛青的合葬墓位置相當,且同冢同批出土的器物上均刻有“陽信家”字樣。因而,有人推測該鎏金銅馬是衛青夫婦的陪葬之物。在當代,曾出土過不少秦漢時期的銅、陶、玉、石馬,但鎏金銅馬卻僅此一匹,因而尤為珍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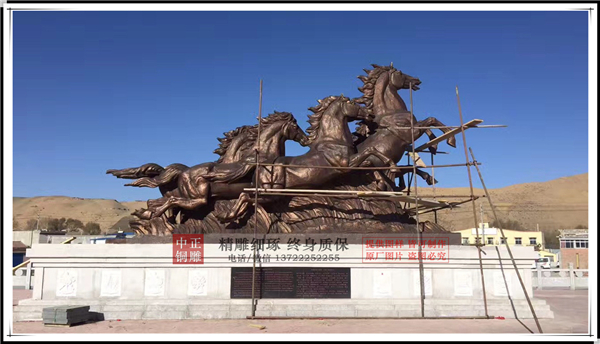
我國古代車馬并舉,所謂御車也就是御馬,所謂乘馬也就是乘車。一車四馬為一乘,春秋戰國時代,按車乘的多少區分國之大小。天子是萬乘之國,諸侯是千乘之國。到了戰國,趙武靈王胡服騎射,匈奴人的騎馬術逐漸流行中原。在冷兵器時代,馬擔當著馱載英雄奔赴疆場的重任,也曾在皇家出行時負責交通、禮儀,還曾在農田里當做畜力被役使。到了當代,馬又承擔起體育競技和娛樂的使命。可以說,馬以天生的速度和聰穎,在賽場上贏得歡呼,以優雅的馬上閑情替代了過去馬革裹尸的命運。

馬文化在中國源遠流長,《山海經》里就有人面馬身神的記述。“力拔山兮氣蓋世,時不利兮騅不逝,騅不逝兮可奈何?虞兮虞兮奈若何!”西楚霸王在《垓下歌》中對他平生最愛——烏騅馬與虞姬都依依難舍;“人中呂布,馬中赤兔”,“董卓將赤兔馬送與呂布,曹操殺呂布后將其轉送關羽。從而,青龍偃月刀與赤兔馬成了關羽的招牌標識;的盧馬是劉備的坐騎,《三國演義》中就有義馬救主的故事,但令其聲名大振的卻是辛棄疾的一句”馬作的盧飛快,弓如霹靂弦驚“;颯露紫、拳毛騧、青騅、什伐赤、特勒驃、白蹄烏為“昭陵六駿”,以或奔馳或站立的浮雕形式,記錄了太宗李世民在大唐創建過程中立下的赫赫戰功;西海龍王三太子觸犯天條當死,受觀世音菩薩點化,化身白馬甘為唐僧坐騎;汗血馬在史書中被稱作天馬和“大宛良馬”,曾作為匈奴人的坐騎令漢高祖在白登之戰中驚鴻一瞥,也曾令漢武帝為其對大宛國發動過兩次戰爭……這些馬以其對主人的忠誠協作和風馳電掣的速度、超強的耐力而名留青史,也成為中國馬文化的精彩篇章。

“馬到成功”即是馬上得天下,是對中國馬的歷史功用的生動寫照;車水馬龍的典故來自漢朝賢后馬氏,她當太后之后,其子想為舅舅們加官進爵,馬氏卻以其兄弟家車如水流、馬如長龍(比擬奢華)而拒絕。金戈鐵馬,戎馬倥傯……正因為有了那一匹匹堅韌、沉默的戰馬,古代英雄才愈發顯得英姿颯爽。

